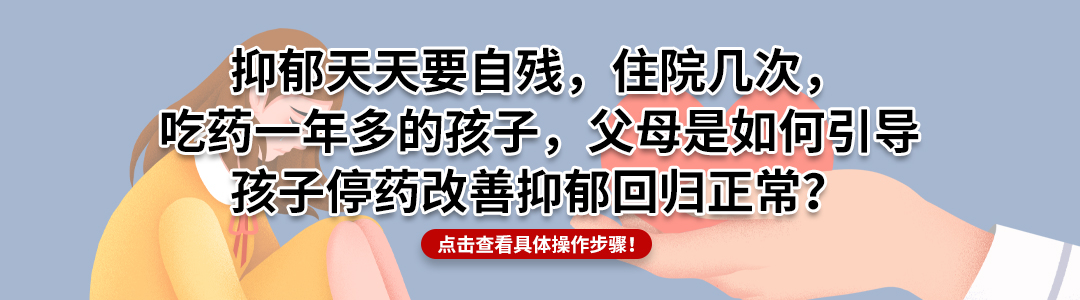“身體被拘禁的77天里,地獄一般的生活比死還要可怕。”
“被綁在床上不能翻身,身體癢了都撓不到,天花板落下的蜘蛛離臉只有幾厘米,但我根本沒法躲開…”
27歲的武田美里回憶起自己13年前的體驗,依然沒法抑制住內心的恐懼。
因為患有進食障礙,14歲的她被送往東京市內的某所醫院,遭到了長達77天的囚禁。

事情開始于初二那年的冬天,美里在和同學聊天后,無意中誕生了想要減肥的想法。
青春期的孩子對一切風吹草動都極為敏感,一句“你體重比我想象中還要重”,就足以成為努力的動力。
但努力不總是有效,只要體重稍微增加,她就會過度控制卡路里的攝取。很快她的例假就出現了問題,身體無力,精神狀態也跟著直線下滑。

父母很擔心她的情況,將她送到了醫院就診。
“雖然當時不懂醫學知識,但我認為既然醫生說是厭食癥,就必須治療。而且聽說是自愿在開放式病房住院,就很放心地同意住院了。”
“大家都為我的身體擔心,我甚至感到很高興。那時在想,住院期間可以給朋友寫信,和家人見面,還想和同病房的孩子搞好關系…”
沒想到,這才是噩夢的開始。

住院當天,她的幻想就被打碎了。她被帶到病房深處像單人牢房一樣的隔離室,里面只有床和便攜式廁所。裝著鐵柵欄的窗被陰影覆蓋,甚至沒法判斷當天的天氣。
入院時首先要做的就是檢查隨身攜帶的物品。手機、iPod、書、紙筆等統統都被收走,甚至隱形眼鏡都不允許帶入。

主治醫生嚴格要求她躺在床上不能隨便動,坐在床邊都會被訓斥。單間內毫無遮擋的便攜式廁所也不允許擅自使用,想上廁所必須得到護士的許可,并在上完后讓護士進行確認。
她被允許的自由,只剩下躺在單間的床上,等待時間的流逝。
治療過程中,主治醫生嚴格要求,提供的食物要至少吃完三分之二。如果完不成就會改用“經鼻胃管”,將營養直接從鼻子輸送到胃里。

示意圖
電視、讀書、聽音樂都被禁止,別說和父母、朋友見面了,就連寫信、傳話都不被允許,在與外界隔絕的日子里,她對醫院和主治醫生的不信任感越來越大。
住院約一周后,她想見父母的懇求被護士拒絕。出于對一系列待遇的不滿,她自己拔掉了點滴,面對趕來的主治醫生爆發出怒火。
她的訴求并沒有得到回應。

4名護士按住14歲女孩的手腳,麻利地用柔道服帶子一樣的又扁又結實的繩子纏在她身上,系在床欄桿下面。
雙手、雙腳、肩膀的身體束縛結束后,醫生從她的鼻孔插入胃管,軟管比胃鏡時插入的那種要更粗更硬,每天24小時,鼻子和喉嚨里一直有堵塞感。
身體痛苦萬分,意識卻極度清醒。
這段時間內,她的一切行為都是在床上完成的。
排尿是以醫療器具自動吸出尿液的形式進行的。直到解除束縛后肌肉力量恢復、能夠自己上廁所為止,排尿器具持續佩戴了2個半月左右。

(示意圖)
經鼻插入胃管的疼痛和不適感太強烈,以致于尿道的疼痛反而那么深,只是覺得異常羞恥。
更羞恥的是排便,因為一直穿著尿布,排便的時候還要叫護士,讓護士脫下尿布,在屁股和床之間放上便盆。如果3天都沒有排便,會通過灌腸強行排便。
按她的說法,自己經歷的,是“極限的地獄”。

但出院后的她并沒有得到賠償,因為缺乏有效的證據,她無法證明自己在院內受到過虐待。
醫院判斷為,如果中止拘禁,她可能會自己拔掉點滴,并且產生自殺傾向,有自傷行為發生的可能。他們無法給出人身控制之外的方法,因此只能繼續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她無法證明當時自己的狀態已經奄奄一息,“精神治療”像是一個巨大的黑箱,遮住了內里的一切事實。
日本茨城縣30多歲的女性櫻井春香,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強行監禁。
幾年前她突然被一群陌生壯漢強行拉上了面包車,拉到精神科醫院隔離治療,經歷了痛苦的辱罵和威脅。
櫻井于2016年未婚生下長子,成為單身母親。

接受采訪的櫻井春香(化名)
但兒童福利相關機構從她懷孕后期仍在工作、沒有準備嬰兒浴室、租住的房間只有9平米大小等方面,判斷她沒有養育孩子的能力。
按市政府要求,這種情況下,孩子將由相關機構統一管理。
櫻井無法接受市政府強行帶走孩子的要求,和相關人員發生過多次爭執,最終爭奪回了孩子的撫養權。
但生活卻并沒有恢復平靜。這之后的一天,走在路上的她被市職員要求“好好談談”,在她進入職員的面包車之后,幾個陌生壯漢突然接管了車。

事后她才知道,這些壯漢是所謂的“民間移送業者”,專門幫忙處理一些官方不方便執行的運輸任務。
而她所乘坐的面包車的終點,是市里指定的精神科醫院。
以抗拒市內規定、不交出孩子為由,櫻井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但她卻并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治療。

最開始,她被帶到只有一床被褥和日式廁所的隔離室,就這樣關了4天。
之后就是醫生們無止境的敷衍。而在這家醫院,輕癥患者是要照顧重癥患者的。調解住院患者之間的爭吵、讓夜間吵鬧的患者冷靜下來、讓出門的癡呆癥患者回房間…這些任務竟然落到了櫻井的頭上。

她被禁止和外界取得聯系,而出院的條件也越來越迷,最終,她又被移送到照顧殘疾患者的福利院——“集體之家”。
在那里,她每天被強迫做6個小時左右的制造工作。福利院的經營者在入住者不愿意進入工作間時,使用備用鑰匙進入休息房間對入住者進行辱罵、威脅。
等她真正恢復自由,和孩子再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后了。

“不僅和孩子分開,還在沒有經過正規檢查的情況下被強制送入精神科醫院,甚至還被強制移居到照顧殘疾人的設施。”
“主導這一切的行政部門和遵從這一行為的醫院和從業者們,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這之后,櫻井向茨城縣、決定移送的市、精神科醫院和民間移送業者,以及殘疾人集體之家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
市政府方面雖然主張移送不是強制性的,但從她的遭遇來看,借助精神病癥來掩蓋一切的行為,顯然無法自圓其說。
什么情況下能強制控制“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呢?一般來說,只有在有資質的精神保健醫生認為沒有其他方法的情況下,才能破例控制患者的自由。
但近年來,日本精神醫療領域的人身控制事件發生率倍增,放在世界范圍內也屬于顯著偏高的程度。
這種情況下,精神病醫院成為掩蓋一切不合理治療、關押行為的“黑箱”,被強行關押在箱子里的“患者”,面對的是難以忘記的痛苦。

日本的醫療和行政被賦予了很大的裁量權,所以即使收到過投訴,也有可能沒有進行適當的處理,更沒有機構對此進行客觀的審查。
行政部門不會正面應對,而是委托醫療機構或委托民間企業通過移送等方式,采取應對療法,或干脆直接掩蓋。

而醫療方面也認為長期住院可以增加收入,所以總是讓“病人”住院,在不考慮具體狀態的情況下進行所謂的治療。
于是我們看到,有人經歷了77天地獄般的捆綁束縛,有人被當成勞動力輾轉于各個機構,有人被關押了4年,就連想和家人說句話都無法實現…

今年,他們的經歷被出版成書,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其中的黑暗。
而至于精神醫療被“封閉”起來的情況會不會得到改善,外界的目光又能不能最終投射進這個一切不合理之事都被掩蓋起來的“黑箱”
或許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