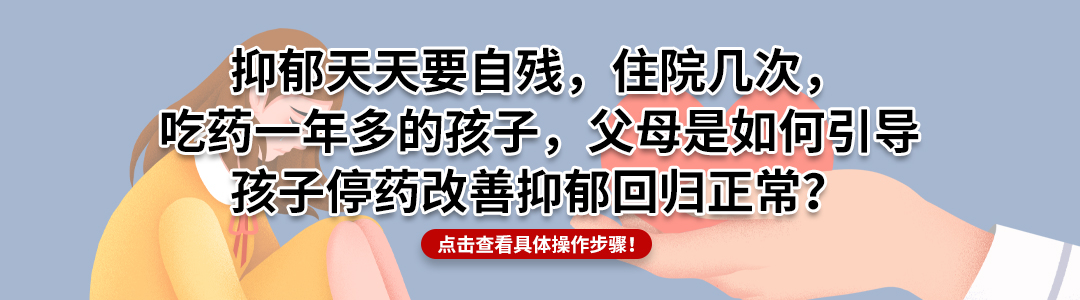高三那年冬天,胡果(化名)在家里割腕了,這是她第一次割得那么深,鮮血直流。
不知道是天氣太冷,還是割的位置不對,血自己止住了。她想,“行,老天爺不開眼。”下午還要繼續上課,胡果清理了現場,用一個創可貼遮住傷口,神色如常地去了學校。
如今,胡果已21歲,這道手腕上淺紅色的刀割痕,依舊依稀可見。她在2018年才被確診為重度抑郁,但從初一開始,自我傷害的行為已持續了10年。
2020年9月1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印發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方案確定了試點地區到2022年的工作目標,任務中特別提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像胡果這樣患有抑郁癥青少年,正在慢慢被看見。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醫學”微信公眾號中的科普推文。
“克制不住自己,就像吸毒一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11月5日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大約每五個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遭受心理健康問題的困擾;在15至19歲的青少年群體中,自殺位列第二大死亡原因。
胡果承認自殘是痛的,但是痛感幾乎成了唯一起作用的發泄方式。“感覺自己是一副軀殼,需要一點疼痛來找到存在感。”
自殘行為是抑郁癥常見的臨床表現,相比于成年患者,在青少年患者中出現的比例更高。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崔夕龍表示,“可能半數以上的孩子會有自殘的行為。”
崔夕龍主要研究青少年抑郁癥方向,在她看來,自殘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它是自殺行為高風險的預測指標,孩子如果情緒繼續走下坡路,或者說哪一次割得再深一點,很容易出意外。”
正是因為體驗過自殘這種不受控的上癮感,胡果也想盡力拉他人一把。
“我堅決反對別人嘗試自殘,一旦產生依賴,會克制不住自己,就像吸毒一樣。”每次看到有網友想要自殘,她總是盡量用幽默輕松的語氣留言,“我說,‘姐妹,相信我會留疤,你知道這個疤有多難祛嗎?’”
“我會說具體的事情,讓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結果,而不是自殘的過程。”這樣的勸說有時候有用,有時候沒用,但她希望“能少一個人就少一個人”。
“真正需要做的是,回歸自己的生活”
通過瀏覽網絡上的一些說法,湘湘(化名)在初三意識到了自己的“不對勁”和抑郁癥有關。進入高中后,她更加喜歡一個人呆著,網絡成為她了解世界的主要通道。
像湘湘這樣通過網絡了解抑郁癥的青少年患者很多。據崔夕龍觀察,目前的一個普遍現實是,孩子比他們的家人更了解抑郁癥,孩子的自我識別意識正在增加。
崔夕龍明顯感覺到,近兩年,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在青少年時期就得到確診的比率明顯上升。這同時得益于整體社會意識的覺醒。青少年自殺的相關報道引發了熱烈的公眾討論,各大網絡平臺也進一步助推了相關科普宣教工作。
但網絡是一把雙刃劍。移動設備的普及使兒童青少年得以與海量的網絡信息直接接觸,但是他們的心智尚未成熟,再加上學業壓力,非常容易導致不良情緒的出現。崔夕龍語氣無奈,“這也是目前我們兒童精神科醫生很頭疼的地方。”
現在,胡果很反感大批抑郁癥患者聚集的網絡群組,“一堆深陷泥潭的人在一個群里的時候,那個群本身就會成為一個泥潭,大家都在沉淪。”
在她之前待過的患者群里,有很多懵懂的孩子。一次,一個初中升高中的妹妹在群里尋求幫助,胡果告訴她,最好的辦法是明天就去看醫生。
而今年疫情最嚴重的時期,鋪天蓋地的新聞又讓她數次陷入情緒的泥潭,后來,她不再緊密關注時事。“真正需要做的是回歸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網絡上給自己制造焦慮。”

湘雅二醫院精神科兒童青少年門診候診區。
“倡導家長堅持用理解和傾聽的姿態,讓孩子敞開心扉”
理論上,青少年抑郁癥成因多樣,包括遺傳的生物學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但依崔夕龍的門診經驗,“遺傳成因的病例較少,更多的孩子患病是因為缺少足夠的社會支持。”
家庭支持是青少年社會支持系統里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而屬于胡果和湘湘的這部分并不完整。
胡果的父母都是控制欲很強的人。他們全盤掌控女兒的吃喝拉撒:偷看她的日記,限制她的交友,甚至“買通”她的朋友作為探子……
“無可否認,他們絕對是愛我的,但是那種愛太讓我窒息了。”初中三年里,她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好覺,晚上總是偷偷地哭,枕芯上有著一圈又一圈的淚痕。
湘湘也不愛和父母說話。湘湘從小性格內向,初中日漸加重的學習壓力,成為了不良情緒最初的導火索。加之與父母溝通不暢,和同伴交往中受到誤解和背叛,多方面的壓力讓她無所適從。
升入初三后,她通過班主任把問題反饋給了父母。“我們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剛開始她情緒不好,我們以為只是青春期的情緒不穩定。”湘湘媽媽眼圈泛紅,聲音里都帶著哭腔,“每次她說和我們有代溝,我都會哭,很希望她能快點好,但是她不愿意跟我們溝通。”
為了讓女兒快點好起來,這是一家人第三次從永州趕到湘雅二醫院。
崔夕龍診室接待的兒童青少年,80%以上會要求父母去診室外等候,有相當一部分孩子表示從未主動和父母吐露過心理情況。
“不是所有的孩子一開始都不愿意和家長溝通的。事實上大部分家長還是很難做到絕對的尊重,更多是說教,孩子會有一點反感。”崔夕龍倡導家長用堅持理解和傾聽的姿態,慢慢地讓孩子卸下防備、敞開心扉。

長沙市周南中學的心理咨詢室。(圖片來源于受訪者)
“預防和解決青少年抑郁癥的問題 需要社會的多方關照”
預防和解決青少年抑郁癥的問題,僅僅依靠孩子自救與家長反思顯然不夠,還需要社會的多方關照。
在學校層面,崔夕龍建議,“至少要有能找著的心理咨詢老師,當一個孩子出現情緒問題,有一個便捷的地方先去表達和接受評估。”
事實上,國家早已有相關明文規定。教育部印發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2012年修訂)》規定:每所學校至少配備一名專職或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并逐步增大專職人員配比。
長沙市周南中學的心理咨詢室周一至周五午休時間開放。心理老師封蕓帙介紹,中學心理健康工作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心理老師會通過交談和相應的量表來監測孩子的心理狀況,如果顯示抑郁值相對較高,會推薦家長到正規醫院做檢查。
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崔夕龍希望能建立健全學生心理問題的保障機制:重視科普宣教,提高預防和早期識別的意識;建立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綠色通道,提供便捷的心理求助熱線和專業的醫生。她透露,目前湘雅二醫院正著力在醫院內部建設青少年兒童心理服務中心,方便老師直接將孩子轉診到醫院做評估。
大學畢業后,胡果成為了一名圖書編輯。父母的控制已經減輕很多,也不再總是批評她。但少年時造成的傷害永遠不可能被彌補,現在她暫居長沙,很少主動和父母聯系,只是偶爾打電話問候他們的身體狀況。
剛成為高中生不久的湘湘,已經對未來有了朦朧的勾畫。關于自己的病情,她認為只有專業醫生才是最有幫助的人,所以她以后也想學習心理學。抑郁癥不可避免地對學習狀態產生了不良影響,但她還是想往這個方向努力,因為真正經歷過,她覺得自己“可能會有一些經驗去幫助這些人”。